四, 04/08/2021 - 15:57 — lac-adm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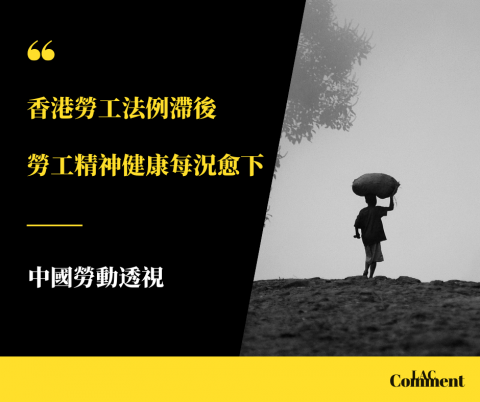
2021-0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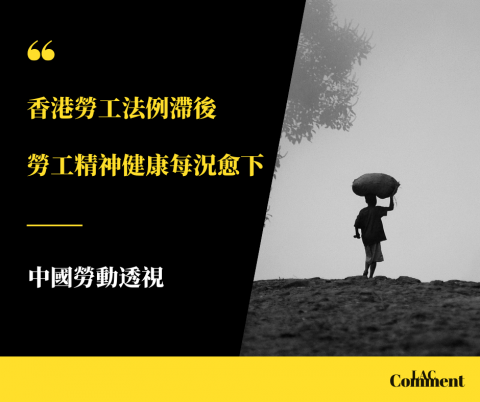
一、背景
香港勞工的工時過長、精神壓力過大已經是大多數港人習以為常的情況。在眾多工時及工作壓力的調查排名中,香港亦經常高居榜首,勞工狀況令人堪憂。 早於2010年,立法會議員曾於會上討論將《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範圍擴大至涵蓋與工作有關的精神疾病 ,當時已有議員指出勞工法例給予勞工的保障並未涵蓋由工作直接引致的精神疾病或工作意外導致員工的精神創傷。當政府被問及會否將壓力症候羣列為職業病時,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搪詞表示:「勞工處會繼續注視國際上在這方面的發展,並按本港的實際情況,考慮是否需要修訂《條例》,將創傷後壓力症候羣列為職業病。」
如今十年過去,香港的勞工法例依然滯後,面對職場帶來的精神疾病,僱員面對苦無申索渠道或是現行的判傷門檻過高的困境,勞工精神健康每況愈下。 本年初,香港民意研究計劃聯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就「工作與精神健康」訪問香港在職人士,研究發現超過三成(35%)勞工經常因工作感到精神困擾,當中工作量大、工作要求高、工時長更是主因。
二、香港的《僱員補償條例》
在《僱員補償條例》下,如僱員因工或在工作期間受傷或死亡,僱主須按照法例第5條向僱員支付賠償。立法會紀錄顯示,該條例自制定以來,政府雖曾多次就補償金額作出修訂,惟補償原則和涵蓋範圍則一成不變。
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結構改變,香港製造業式微,港人現大多從事工時長、壓力大的服務行業,僱員須長時間工作,加上工作量大 ,容易招致過勞、焦慮、抑鬱等精神疾病。在新冠肺炎衝擊下,不少員工在家工作,更大的工作彈性往往換來更長的工時。然而,《僱員補償條例》卻未能一一回應僱員面對的困難。至今,《僱員補償條例》中附表一(「損傷類別」)及附表二(「職業病類別」)依然未包括因工而致的精神損傷或疾病。
三、立法難關重重
雖然僱員面對職場壓力大而患上精神疾病的例子俯拾皆是,但要擴大職業病範圍至涵蓋精神疾病卻絕非易事。在立法角度而言,政府有一套嚴格的標準:本港從事某種職業的工人有否罹患該疾病的顯著和確認的風險;以及可否合理地推定或確定在個別個案中該疾病與該種職業的因果關係。
換言之,政府須確定某一特定行業的從業員有顯著或已確認的風險會患上該精神疾病,並且在工作及精神疾病兩者之間存在可合理推定的因果關係才會考慮把某一疾病列為職業病。誠言,就是否把某一疾病納入職業病範圍而設定一套準則是可以理解的,但隨著經濟模式轉變,政府依然沿用此過時的框架實在是置勞工的真實需要於不顧。
第一,精神疾病並不只存在某特定職業中。如眾多民調所示,工作時數、工作量、上司與下屬之間的關係等等都有機會導致勞工出現過勞、焦慮、抑鬱等病徵;在香港,可謂不同行業都普遍存在員工經常需要超時工作的問題。政府亟需審視的是現時的立法標準是否仍能反映實況,並且回應得到勞工面對的困難。如政府一直沿用一成不變的準則去考慮能否將精神疾病涵蓋到職業病範圍中只是刻舟求劍。
相反,台灣早已就職場上可能出現的社會、心理性危害制定《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協助勞資雙方判斷精神疾病與工作的相關性;《指引》列出幾項容易引起工作壓力的因素,包括(一) (嚴重的)疾病或受傷;(二) 與業務相關,引發重大傷亡事故、重大事故;(三) 造成會對公司經營產生影響等的重大工作疏失;(四) 被無理地要求離職;以及(五)(嚴重地)受到刻意讓人厭煩/生氣的騷擾、霸凌或暴力行為,並明確指出這些壓力源可能來自不同的工作。
筆者上文已討論台灣的經驗,在此不再贅述。但筆者反覆援引台灣為例無非是希望強調政府需極力解決目前法律的不足,從頭審視納入職業病的準則和機制,並非以過時的標準逃避立法需要。
第二,一直以來,政府均以難以確立工作和精神疾病之間的聯繫為由來逃避立法。誠言,精神疾病的成因複雜,一時間未必容易證明疾病由工作引起,加上員工的抗壓能力和性格都影響精神疾病的出現。但政府以此為由拒絕探討職場和精神疾病的關係是不合理的,做法亦漠視員工在職場上面對的困境。
201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法院在一宗精神疾病索賠個案[1]中曾仔細探討工作和精神疾病之間的因果關係。代表政府的一方強調,除了急性精神壓力 (acute mental stress) 外,現時暫未有一套客觀可靠的方法處理精神疾病與工作間的關係[2]。代表勞工一方力陳證明兩者關係只是困難而非不可能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3], 並指出上述困難於許多涉及身體損傷的賠償案件同樣存在[4]。
法庭審視過訴訟雙方的案例和專家意見後,最終認同勞工代表的意見,表示壓力因素出現的時間順序對精神健康的影響可以透過申索人的病情發展和其他知情者的紀錄來判斷,加上心理醫生的培訓和臨床訓練亦可協助法庭判斷工作和精神疾病間的因果關係。[5]事實上,縱使僱員某些個人因素會影響其精神疾病的出現,但如同代表勞工一方在案中所言,這只是增加法庭判斷因果關係的難度,而非使之不可能,法庭最終還是可以倚靠員工的求醫紀錄和臨床心理醫生的診斷去判斷工作和精神疾病間的因果關係。
第三,政府不應對精神疾病和生理疾病有差別對待。在上述案件中,法院判定安省的職業安全及保險法案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 “WSIA”) [6]中對精神疾病申索所訂的限制違憲,表示立法機關不能就精神疾病 (mental disease) 和生理疾病 (physical illness) 訂立兩套不同的申索標準,否則會構成歧視。
根據WSIA法案,勞工的申索權限只限於因工作或在工作過程中發生的意外所造成的人身傷害;第13(4)和(5)款[7]額外規定如果勞工在工作期間因突發及不可預料意外創傷事件而產生應激反應及壓力(“A worker is entitled to benefits for mental stress that is an acute reaction to a sudden and unexpected traumatic event arising out of and in the course of his or her employment.”) ,員工可就此提請賠償。法庭認為法案的寫法其實限制了員工只能在狹窄的情況下,即就突發及不可預料意外創傷事件而引致的壓力索賠,但員工就生理創傷,不論是意外或蓄意的行為索賠則不受此限。法庭亦指出條款使由非意外 (sudden and unexpected) 的創傷性事件 (traumatic event) 而致的精神疾病不受保障[8]。
雖然案件更多的是討論立法機關就精神疾病申索加諸生理疾病賠償條款沒有的限制是為不公,但背後的法理原則同樣值得我們深思,為何同樣是由工作導致的創傷,員工遲遲未能就精神疾病獲取應得的賠償?綜觀香港的勞工法例,目前即便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仍然未被納入職業病列表中,落實僱員更完善的保障遙遙無期。試問,若連相關的勞工法律條文都欠奉,又何談條例有否構成歧視不公的基礎?
香港作為一個蜚聲國際的大城市,勞工權益卻是毫無保障可言,最高工時、勞工集體談判權等議題被港府一拖再拖,加上工會制度未及完善,僱員大部分時候在職場上只是孤軍作戰,員工如欲就精神疾病索償也只能訴諸冗長而費用高昂的訴訟。面對如此困境,政府實在有必要認真審視現行的法律框架,研究落實將精神疾病涵蓋到職業病列表中。唯有這樣,僱主才會正視職場壓力為僱員帶來的精神創傷。
注:
[1]Decision No. 2157/09, [2014] OWSIATD No. 1048
[2]Ibid., para [120]
[3]Ibid., para [84]
[4]Ibid., para [99]
[5]Ibid., para [156]
[6]s 13(4) and (5) of WSIA
[7]s 13(5) – “A worker is entitled to benefits for mental stress that is an acute reaction to a sudden and unexpected traumatic event arising out of and in the course of his or her employment.”
[8]n 10, para [186]
*版權為中國勞動透視所有,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議題聚焦:
